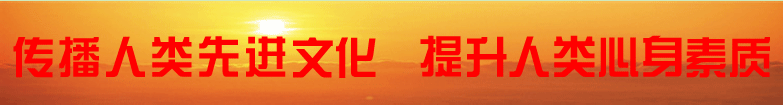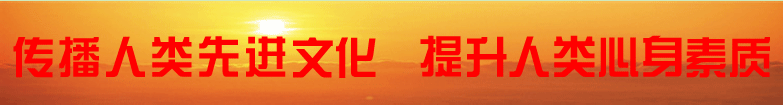|
|
| 惊涛骇浪涤尘心 |
|
<七发>是牧乘的独创,在汉赋中自成一体.他是借楚太子有病,吴客去问询,说七事以启发太子,让他能够从安逸享乐的精神牢笼里超脱出来,把自己的心病治好.遐迩有名的广陵曲江:徒观水力之所到,则恤然足以骇矣.看那水力所凌驾的,所拔起的,所播扬和激乱的,所结聚和滚动的,所涤除和洗荡的不正是对人的心灵的冲击吗.
"秉意乎南山,通望乎东海;虹洞兮苍天,极虑乎崖矣"
巨浪滔滔,气吞大荒,状似奔马,犹如擂鼓.扫荡南山,击溃北岸,颠覆丘陵,崩坏江堤.如此浩观满目,喧涛盈耳的波澜迭起,给人以神秘莫测惊醒.
观涛者随江潮而流揽无穷,将心神聚集到旭日升起的东方,又见浪头飞速下驰,纷乱曲折地奔泻,纠结着一去不回.目迷心乱的观涛者欲寻求浪踪涛迹,五脏如同经过冲刷一样,手足,发齿,颜面好象经过涤汰般地干净,江涛激荡,使人振奋,排除疑惑而亮听聪,改变人的精神面貌.即使有缠绵日久的老病,也会伸腰挺胸,昂首阔步,跛脚者提足走路,失明者睁开眼睛,失聪者掰开耳朵,所有的患者竭力克服生理上的困难,看一看浩浩荡荡的江潮.既然观涛能如此调动残疾者的兴趣,何况那些小小烦闷昏醉病酒的人呢.
修道之人在养心
宋·白叟玉蟾子辑——凡参玄宗不难得手,难从性宗参入。如从此入,便得渊源。倘错行路径,如书空寻迹,披水觅路矣。
修玄之理,可以意会,不可以言传,古人章句之中隐隐在焉。天不言而四时行,人身阴阳消息,人不能使之然也。
大道之妙,全在凝神处。凡闻道者,宜领此意求之。凝神得窍,则势如破竹,节节应手。否则面墙而立,一步不能进。
学道之人,须要海阔天空,方可进德。心宜虚空,神宜安定,能使心不动,便可立丹基。 学道之人,以养心为主。心动神疲,心定神闲。疲则道隐,闲则道生。胸次浩浩,乃可载道。
邪说乱道久矣,采战、烧汞、搬运皆邪道也。年少者、不笃信者、遑遑趋利者,皆未易言此道。欲修此道,先宗一淡字。仙凡界、人鬼关,全在用功夫。然用功夫者,如擒狡兔然,稍懈则兔纵,稍紧则兔死。须于空虚中觅之,否则何足言功夫哉。
凡人心不内守,则气自散。若能时时内观,则气自敛,调养脏腑,久之神气充足。古云:“常使气通关节透,自然精满谷神存”。
静时炼气,动时炼心,下学之功毕矣。须节欲。先天必须后天定。动时茫茫,不如此心久在腔子里。学道者要先知收心法,再言静功。欲学玄功,须先时时瞑目,一日间静坐几刻,再来问道。 聪明智慧不如愚,学人只因伶俐二字,生出意见,做出许多坏事。今欲收拾身心,先从一个愚字起。
天之生人,人之所以生而不死者,于穆不已也。人若无此不已,则气绝矣。故天地以气机存,人亦以气机生。能炼住气机,便与天地同寿,便不息了。不息则久,中庸言之矣。
定其心神,方可言道。要入玄关,须用定力。定则静,静则生。不但静中能静,必须动中能静,方见功夫之力。神定,内一着也。事来心应,事去心止。气定,外一着也。
语谨形正,语端气峻。下学要紧处,全在正气安神,忘心守口而已。修道原从苦中来,但得清闲处便清闲,此即是道。且更须忙里偷闲,故人能偷闲便有闲。不然,则终身无宁晷矣。
心乃一身之主,故主人要时时在家。一时不在,则百骸乱矣,所以学道贵恒。始勤终怠,或作或辍,则自废也。
忧心虚病自招鬼
东汉王充在<订鬼>一文,首先提出"鬼"产生于人的畏惧心理,即会有存想,继而幻想迭起目虚见,心病招鬼,鬼扰人.万病生于心,只在一念间.大凡天地之间,出现鬼,并不是人死后的精神变成的,都是人们思念想象所造成的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?是由于疾病(的折磨)。人生了病就会忧愁害怕,忧愁害怕就好象看见鬼出现了。凡是人无病时就不会怕这怕那。所以得了病躺在床上,就害怕有鬼到来。一害怕就会老是想,想久了就会使得视觉错乱,恍恍惚惚地看见鬼了。
用什么来验证呢?古书上说:“伯乐学习鉴别马的时候,由于用心过度,看到的东西,没有不是马的。宋国庖丁练习解剖牛的本领,三年以后,在他的眼里,没有见过活牛,所看到的全是分解了的)死牛。”这两个人都是专心到了极点。胡思乱想,自然就会看到怪异的事物了。人病了看见鬼,如同伯乐看见马,庖丁看见牛一样。伯乐和庖丁看到的其实不是真正的马和死牛,由此可见病人所看见的也并不是什么鬼了。
病人身体困倦极了,身体疼痛,就说是鬼拿了棍捧鞭子欧打他,好象看见鬼拿着锤子、锁链、绳索,站着守在他的身旁。(这是因为)病人身体疼痛,心里害怕,才虚幻地看见这些的啊。刚得病时心里惊慌害怕,(就好象)看见鬼来了;病重一些就怕死,好象看见鬼在发怒;身上因病感到疼痛,(就好象)看见鬼在打:这都是由于想得过多,产生虚幻的感觉造成的,并不是真有那样的事实。
专心想念事物(的结果),有的表现在视觉上,有的表现在说话上,有的表现在听见的声音上。表现在视觉上的,(好象)看见鬼的形状;表现在听觉上,(好象)听到了鬼的声音;表现在嘴上,(就会)说出鬼的事情。(因此)白天会看到鬼的出现,夜里就会在梦中听到鬼的声音。独自睡在空房之中,如果感到有些害怕,就会梦见好象有人按住他的身体哭泣呢!睡醒见到鬼形,躺下听到鬼声,都是由于精神作用引起的;害怕和想象,都出于同样的情况。
刘勰养心在诚信
刘勰是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。字彦和。早年笃志好学,家贫不婚娶,依沙门僧佑,精通佛教经论。梁武帝时,历任奉朝请、东宫通事舍人等职。晚年出家为僧,改名慧地。南齐末年,写成《文心雕龙》50篇,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。
其《新论》中用大量笔墨,从哲学、史学的角度论说了信道德规范。
“信者,行之基,行者,人之本,人非行无以成,行非信无以立。故信之行于人,譬济之须舟也,信之于行,犹舟之待楫也,将涉大川,非舟何以济之,欲泛方舟,非楫何以行之。今人虽欲为善而不知立行,犹无方舟而济川也,虽欲立行而不知立信,犹无楫而行舟也,是适郢土而首冥山,背道愈远矣。自古皆有死,人非信不立,故豚鱼著信之所及也。允哉斯言,非信不成。齐桓不背曹刿之盟,晋文不弃伐原之誓,吴起不亏移辕之赏,魏侯不乖虞人之期,用能德光于宇宙,名流于古今,不朽者也。故春之得风,风不信则花萼不茂,花萼不茂则发生之德废;夏之得炎,炎不信则草木不长,草木不长则长赢之德废;秋之得雨,雨不信则百谷不实,百谷不实则收成之德废;冬之得寒,寒不信则水土不坚,水土不坚则安静之德废。以天地之灵气,不信,四时犹废,而况于人乎?昔齐攻鲁,求其岑鼎,鲁侯伪献他鼎而请盟焉,齐侯不信,使柳季,云是则请受之,鲁使柳季,柳季曰:‘君以鼎为国,信者亦臣之国,今欲破臣之国,全君之国,臣所难也。’乃献岑鼎。小邾射以邑奔鲁,鲁使季路要我君无盟矣,乃使子路辞焉,季孙谓之曰:‘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子之一言,子何辱焉?’子路曰:‘彼不臣而济其言,是不义也,由不能矣。’夫柳季、季路,鲁之匹夫,立信于衡门而声驰于天下,故齐邾不信千乘之盟,而信二子字言,信之为德,岂不大哉!秦孝公使商鞅攻魏,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,鞅谓昂曰:‘昔鞅与公子善,今俱为两国将不忍攻,愿一饮宴休二师。’公子许焉,遂与之会。鞅伏甲虏之,击破魏军。及惠王即位,疑其行诈,遂车裂于市。夫商鞅秦之贵臣,名重于海内,贪诈伪之小功,失诚信之大义,一为不信,终身犹卒至屠灭,为天下笑。无信之弊岂不重乎!故言必如言,信之符也,同言而信,信在言前,同教而行,诚在言外,君子知诚信之为贵,必忱信而行,指麾动静,不失其符,以施教则立,以莅事则正,以怀远则附,以赏罚则明。由此而言,信之为行,其德大矣。”
自然之心信常在
傅玄,西晋哲学家,也是文学家。字休奕。学问渊博,精通音律,擅长乐府。在哲学上,认为自然界是按照“气”的自然之理而运动的,人的“德行”不能代替自然规律的作用,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成是一种自然过程,批判了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玄学空谈。所著《傅子》一书,集中反映了其哲学思想。关于信,傅玄说:“盖天地著信,而四时不悖,日月著信,而昏明有常。王者体信,而万国以安,诸侯秉信,而境内以和,君子履信,而厥身以立。古之圣君贤佐,将化世美俗,去信须臾,而能安上治民者,未之有也。夫像天则地,履信思顺,以壹天下,此王者之信也;据法持正,行以不贰,此诸侯之信也;言出乎口,结乎心,守以不移,以立其身,此君子之信也。讲信修义,而人道定矣。若君不信以御臣,臣不信以奉君,父不信以教子,子不信以事父,夫不信以遇妇,妇不信以承夫,则君臣相疑于朝,父子相疑于家,夫妇相疑于室矣。大小混然而怀奸心,上下纷然而竞相欺,人伦于是亡矣。夫信由上而结者也,故君以信训其臣,则臣以信忠其君,父以信诲其子,则子以其信孝其父,夫以信先其妇,则妇以信顺其夫,上秉常以化下,下服常以应上,其不化者,百未有一也。夫为人士,竭至诚,开信以待下,则怀信者欢然而乐进,不信者赧然而回意。老子不云乎,信不足焉,有不信也,故以信待人,不信思信,不信待人,信思不信,况本无信者乎?先王欲下之信也,故示之以款诚,而民莫欺其上,申之以礼教,而民笃于义矣。夫以上接下,而以不信随之,是以亦日夜见灾也。周幽以诡烽灭国,齐襄以瓜时致杀,非其显乎!故祸莫大于无信,无信不知所亲,不知所亲,则左右尽已之所疑,况天下乎!信者亦疑,不信亦疑,则忠信丧心而结舌,怀奸者饰邪以自纳,此无信之祸也。”
|
|
|